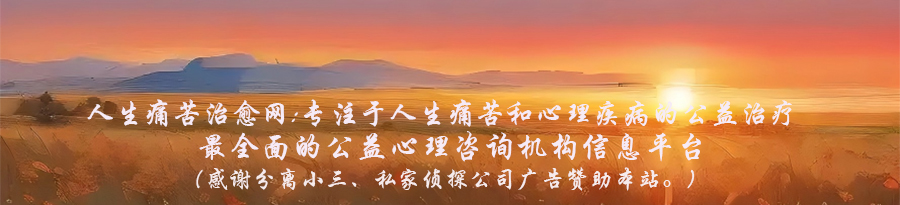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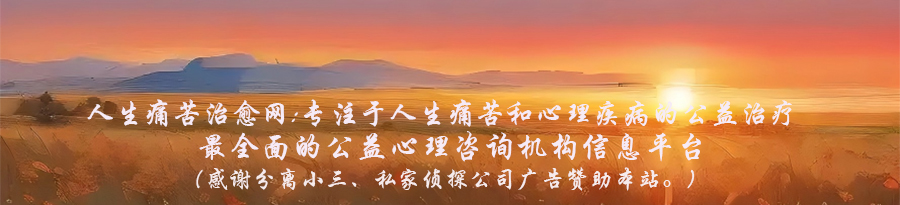
从避而不谈,到“是时候告别了,要想想接下来该怎么生活了”。
采访刘老师时,是一个秋天的傍晚,北京那天罕见地下了雨,异常寒冷。他用低沉而平缓的口气说起了十一年前的一次意外:2008年夏天,儿子刘丹因为暑期集体活动需要打了一剂预防针,打针之后就开始有点低烧。当时孩子正要面临一场大考,父母心想是临近考试压力太大了,考完休息一阵子应该会好。孩子顺利考完了试,约了几个朋友一起周日出去玩,闹钟定了早上七点半。结果那天早上闹钟闹了几次,他都没醒来……等父母进房时,孩子已经没有呼吸了!
……一场毁灭性的灾难,来得竟是如此不可思议的突然。
那一年,孩子16岁。这种震撼、痛苦、悲伤、绝望、怀疑……大概什么语言也无法描述。他说:“我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仿佛在梦里。我就只想知道,为什么?为什么?”
当时,他们并不知道是预防针的问题,以为是心脏猝死;后来经过医学研究,才揭开了谜底,发现是预防针引发的器官损伤。
科普:子女死亡的原因中,有3种对父母打击最大:第一是自杀,第二是他杀,第三是不明原因的死亡。因此,对刘老师夫妇来说,寻找答案,是当时一个最强烈的信念。
他曾写下这样悲痛的句子:“我唯一的孩子,那样健康活泼、风华正茂的孩子,承载着我们16年的哺育的孩子,凝聚了所有爱和心血的生命……就这样没有任何征兆,离开了我们。”
葬礼之前,他为孩子写追悼词。努力回忆过往的许多事,带着沉重的痛苦写下这一切,似乎像是帮孩子说完他未曾说的话。这个过程,会一次次感觉到,孩子还在身边,并没有离去。
参加葬礼,是他们当时面临最痛苦的一个选择。因为,对于每一个失去挚爱的人来说,葬礼是一场无法缺席的告别;但是心理学家也告诉我们,没有一位失去孩子的父母是自愿参加葬礼的,都是被“逼着”去的,内心太折磨了。“在葬礼之前,我一直都觉得很不真实,就好像做梦一样,日夜浮现的都是孩子还在的样子。但是直到在殡仪馆看到孩子冰冷的遗体,我才被打回现实。一个星期没有一滴眼泪的我,突然在儿子遗体面前哭倒,我近乎崩溃掉,站也站不住。因为我知道,那是我见孩子的最后一面了。”
朋友们把他“架”到了休息室里,给他吃了镇静剂,等他缓过来,才有力气读出追悼词。在那一刻,他突然意识到:时间到了,是时候告别了,我要想想接下来的生活了。
科普:人们往往忽略了,葬礼是哀伤治疗很重要的一步:1. 让人把压抑的情绪发泄出来;2. 意识到亲人离去的事实,走出幻觉;3. 让亲友知道真实情况,获得支持。
孩子离开之后,他和妻子每个星期都会去一次墓地。他说,在埋葬着他孩子的墓地附近,还安葬着其他一些年轻幼小的生命。其中一块墓碑上,刻着一个小脚丫子的泥印,这是一个仅仅活了16天的小生命。还有一块墓地埋葬的是一位中年男子,他的父亲每个周末都会来看他,并带来一束鲜花,十多年从未断;有一位老太太天气好时,每次来都会坐上一整天,在那里读书给孩子听,直到夜幕降临,她才不舍地离去。刘老师夫妇每周也会在这里看望孩子,跟孩子说说话,把最近自己做的事告诉孩子。他们想象孩子听到好消息,露出的笑脸……再后来,每一次来墓地,都如同是与一个纯洁灵魂的对话。这种感觉使人特别宁静,没有忧苦,除了儿子的忌日。
刘老师说:“在这座墓园,儿女们来墓地看望已故的父母,大概是每年2~3次;丈夫或妻子来看已故的配偶,每年约4~5次;而父母们来看望孩子,几乎是每周一次,风雪无阻,年复一年。”
听完这席话,我如鲠在喉。我第一次感受到,父爱母爱——不同于人间其他任何一种爱,是一种融进了他们血液和生命、至死都不会消失的爱。
过了很多年,刘老师和亲戚一起外出旅行,在一个游乐场旁边,他突然站住了。因为眼前的游乐场,让他突然想起儿子小时候,他曾带孩子来这里玩过。当时孩子玩得那么开心,他的小脸蛋红通通的,一蹦一跳……“那个画面一直印在我脑海里,我在那里呆呆地怔住了好久好久,现在一切都已物是人非,哀伤不知不觉地从心底泛起……但是大约5分钟后,我已从这种哀伤中抽身而出,回到现实跟亲戚一起继续快乐的游玩。”
科普:刘老师描述的这种状态,是近代哀伤学者常说的“整合性哀伤”——人们带着哀伤和怀念,但依然可以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很多人面对丧亲的哀伤,往往都会期待自己“走出来”,但哀伤心理学家认为,真正的“走出来”,不是不再思念,而是你可以自由地控制自己的思绪。你能够可控地进入哀伤思念、回忆逝去的过往;同时还可以选择面对现实,好好地生活,这才是一种正常而健康的哀伤,也就是“整合性哀伤”。
我第一次听说刘老师,其实是在“首届全国哀伤大会”上(全名为:首届中国哀伤研究与干预国际研讨会)。刘老师以“美国注册哀伤咨询师和哀伤研究者”的身份参加了这次大会。你可能会对他这个身份感到好奇,究竟他是如何从一位失去独子的父亲,成为一个哀伤研究的专家呢?
在大会发言中,他谈起自己房间里的一个镜框,里面镶着一篇儿子小学二年级时写的作文。大概的意思是,如果每个人都给别人分享一份爱,那这个世界将会很美好。“看到孩子的这些话,我觉得他还没有离开。我想去做他想做的事,那样他的生命还会继续发光。”在孩子出事之后,心理学相关的书和科普文章给了他很多帮助,他觉得这些知识能够帮助到“同命人”,于是开始大量学习。家里堆满了上百本哀伤学术专著,通过自学考试,他成为了一名美国“注册哀伤咨询师”。同时,他开始帮助那些跟他有相同经历的父母。他相信这是他儿子所希望看到的。
有一次回上海探亲,他注意到中国非常缺乏“哀伤干预”方面的书籍和文献。丧亲与哀伤,是西方人并不避讳的话题,在美国一个最不起眼的小书店里也能找到“哀伤疗愈”的书,但在规模巨大的“上海书城”,却看不到一本。然而我国有着世界上最大的丧亲人群,每年有近一千万丧亲家庭,人们非常需要哀伤疗愈啊!“我们中国人回避哀伤、不谈死亡,但这偏偏又是我们每个人要去面对的。我希望写一本这样的书,能够帮助到那些跟我有相同经历的父母们。”
于是,刘老师联系到了北京师范大学著名心理学家王建平教授,他们一拍即合,决定为我国丧子父母写一本哀伤疗愈的书籍。为了完成书籍,刘老师辞去了一切工作,没有任何收入,闭门不出六个月。通过查阅海量文献、寻求与国际著名学者的交流和帮助,并通过和大量失独父母的访谈互动,与王教授一起完成了《哀伤理论与实务:丧子父母心理疗愈》。那是国内第一本基于中国文化,把近代哀伤理论与干预方法系统地介绍给中国读者的心理学专著。书中不仅有大量的前沿研究和理论,也有许多非常实用的疗愈方法。这些方法不仅是写给丧子家庭的,也是给每一个经历丧亲之痛的我们。我们都有一天会面临离别,而那天到来之前,我们需要了解哀伤,更需要了解死亡。
说起这本书,刘老师说:“只有爱是不够的,只有专业知识也是不行的。谈哀伤必须要有爱,也要有学术的严谨。我的孩子虽然只走到16岁,但是他的生命轨道与我是同向的。作为父亲,我可以把深植于他生命中对这个世界的爱,在这条轨道上继续延续下去,这就是我的使命。”书序言中,刘老师首先提到的就是他挚爱的儿子——刘丹。在那一刻,也许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更深刻地体会和理解书中的一句话:“哀伤,就是爱。”
最后
在这之前,王建平老师也做过一些关于哀伤的研究,也一直在做国内“失独家庭”的帮扶工作,2016年申请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基于全国调研数据的中国失独人群心理健康援助体系研究》。
关于如何与逝去的亲人保持联结,她告诉我们:当我们的亲人离去,其实我们都在用各种方式继续与他们保持着联结。一方面是外在的联结,例如刘老师提到的,参加葬礼、看亲人的照片、保留遗物、去墓地探望等,现在甚至有人在网上为亲人建一座灵堂,以寄托思念。这些方式让我们与离去的人保持着一种情感上的联结。但有些丧亲者过分地聚焦于这些外在的联结,不能接受逝去的现实,对自己的生活产生阻碍。
还有另一种,是内在联结,例如:回忆对亲人的爱和关心,跟亲人对话、完成逝者生前的梦想、帮助别人等。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联结,让我们感觉到逝去的生命还在延续和发展,在联结的同时能够面对逝去,去适应丧失后新的生活。
现实中,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像刘老师这样,有些父母在做这些的时候非常痛苦,他们聚焦在丧失的伤痛中,觉得亲人还在世,不能接受现实,甚至无法正常生活,可能进入病理性哀伤或者叫延长哀伤的过程……
至于如何分辨健康的、不健康的联结,以及哀伤疗愈的过程到底是怎样的,《哀伤理论与实务》中我们有提到相关的研究。我们对于哀伤的理解,目的是从科学的角度,找到帮助丧亲者的有效的方法。近些年我们一直提到“整合性哀伤”,它告诉我们,“遗忘”并不是处理哀伤的唯一方法,我们需要一种健康的思念和联结——既可以走入回忆,也可以回到现实好好生活。另一方面,心理学的研究发现,那些能够去帮助别人的人,往往更容易从剧痛走向整合性哀伤,这或许是对我们非常有启发的一个结论。
王建平老师
如果要去帮助身边丧亲的人们,应该注意什么呢?王老师说:人在面临重大灾难时,在极大痛苦的情况下,最直接的反应就是生理状况都被扰乱了。因此在帮助丧亲者时,最开始要做的其实是身体和生活上的帮助,例如给他们做可口的饭菜、保证人身安全等,也就是通过有效的陪伴,照顾丧亲者的基本需求。至于心理学工作者的介入,反而是比较后期的工作,也就是说心理干预需要合适的时机。
很多人会用这样的话去安慰丧亲者:“你别难过了”“我理解你”……这其实是不恰当的安慰,丧亲者会在心里说:“你根本不了解我们的状况,不理解我们的想法,走开吧。”甚至有的丧亲者会觉得:“你们是来看笑话的吗”。这样的安慰不仅没有用,反而会加重对方的哀伤。通俗地来讲,在丧亲的最早阶段,聆听和陪伴、照顾好他们的生活起居是非常重要的。
葬礼对于哀伤治疗有特殊的意义,那么是不是丧亲者必须要参加葬礼呢?王老师认为,并不是必须的。在中国文化中,丧葬文化有非常独特的方面。一方面,丧葬是一个告别仪式,让人们真正面对这个事实,从这一点开始,去考虑新的生活;同时,它也是一个很大的情绪冲击。有些人无法去面对这种冲击,也不觉得葬礼是必须的,那么就可以不参加,也许他或她有自己独特的仪式与逝者去告别。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如果他愿意参加葬礼,但是你出于害怕他情绪过激,而瞒着他、不让他去,那么反而会造成更严重的打击;而如果是当事人决定不去参加葬礼,那也是可以的,但是与逝者在适当的时候以恰当的方式告别是需要的。
最后,王老师从研究者的角度,给了我们一些关于现状的思考:其实像刘老师这样的人,是少数。他本身有非常高的受教育水平,而且很有责任心、有使命感,不仅能够自我救助,还愿意帮助别人。而现实中一部分的丧亲者(尤其是失独父母),是关起门来,拒绝外在关怀的。我们能接触到的,基本上都已经是恢复得比较好的人,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反而都见不到,也不愿接触。那么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王老师认为,“同命人”的协助非常重要。同命人是指有相同经历的人,他们能够最大程度了解对方的心理需要、情绪感受。“因此,培训同命人,让他们走在前,我们专业的团队在后面再去给予帮助,是最好的方式。”这是王老师目前的经验和感悟。
对于哀伤,我们需要针对大众的科普教育,死亡教育也在其中。王老师说:“我感到高兴的是,这次的哀伤国际研讨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这个作用,让参会者(辐射到全国)意识到,哀伤是个专业,需要专业的态度来对待。”死亡教育,不应该是直面死亡时的痛苦,而是能够让每一个人,对生和死有合理的期待。这样,我们才能有勇气直面哀伤。
热门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