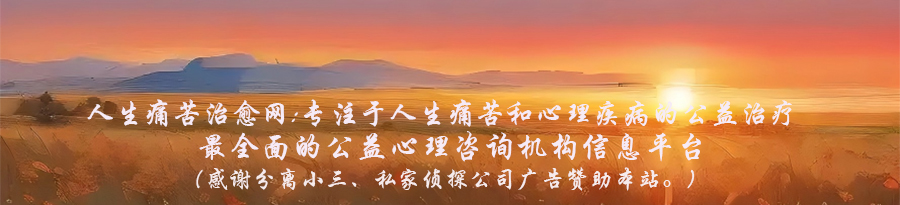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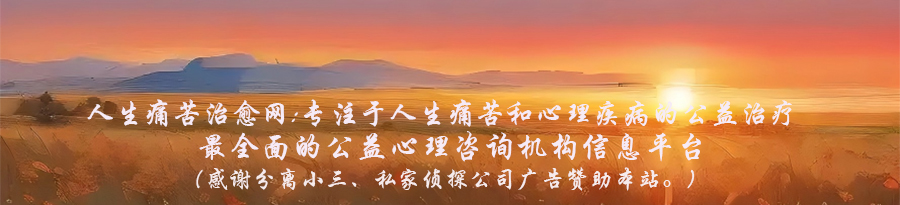
她觉得一切都无所谓,所以生活给她什么,她便接受什么。少年时代,她觉得选择为时过早,而现在已是青年,她又觉得改变为时已晚。这种日复一日的被动与疏离,像一层透明的薄膜将她与世界隔开,她能看见外面的一切,却感觉不到温度,也发不出自己的声音。她活在一种温和的绝望里,既不激烈反抗,也不热烈拥抱,只是任由时间如流沙般从指缝中溜走。
她就要死了,却什么都没经历过。这不是指物理意义上的死亡,而是一种精神上的枯萎与凋零。她的生命如同一本没有书写过的空白笔记本,封面或许精致,内页却一片虚无。未曾为热爱的事物热血沸腾,未曾因深刻的联结心碎神伤,也未曾为了某个目标奋不顾身。这种“未曾活过”的感觉,比死亡本身更令人窒息。
-01-
我也不是非要去死,只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活着。
当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时,我的心被扎了一下。因为它不是呐喊,而是呢喃;不是控诉,而是迷茫。它揭示了一种比痛苦更可怕的境地——意义的真空。痛苦至少证明你还感受着、挣扎着,而这种虚无却让人连挣扎的力气和理由都找不到,仿佛悬浮在无尽的灰色里。
这句话是北京大学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副主任徐凯文老师讲的。在工作中,他遇到了不少这样的北大学子:他们人际关系良好,成绩优秀,生活无忧,家庭和谐,几乎没有童年创伤,是他人眼中的“好孩子”。他们按照社会期待的剧本,完美地扮演着“优秀”的角色,一路过关斩将,抵达了众人羡慕的彼岸。然而,站在山顶,他们环顾四周,只感到一片荒芜与茫然。
但是,他们想自杀。这种念头并非源于具体的挫折或苦难,而恰恰源于一种“无根”的成功。当外在的目标——好成绩、好大学、好工作——逐一实现后,内里的空洞便再也无法遮掩。他们像是精心搭建的积木塔,外表稳固华丽,内里却空无一物,一阵微风就足以让他们感到坍塌的危险。
徐凯文老师将这类个案,称为“空心病”。这是一种价值观缺陷所致的心理障碍,其核心是缺乏支撑其意义感和存在感的价值观。他们不知道“我是谁”、“我为什么而活”,只是在机械地履行“优秀”的程序,内心却与真实的自我、与他人、与世界失去了深刻的联结。
当读《维罗妮卡决定去死》这本书时,我想,这不就是“空心病”么?维罗妮卡的困境,正是这种找不到存在意义与生活热情的典型写照。她拥有一切世俗认为“应该”让人幸福的条件,却唯独失去了感受幸福、创造意义的能力。
24岁的维罗妮卡年经漂亮,父母疼爱,工作轻松,在外人看来,她实在没有自杀的理由。她为自己找的理由有两个:一是生命里的一切均一成不变;二是对这个世界无能为力。第一个理由关乎对生活体验的深度厌倦,每一天都是前一天的精确复制,未来清晰可见,毫无惊喜,也毫无盼头。第二个理由则关乎对自我效能的彻底怀疑,她感到自己像巨浪中的一片树叶,无法影响任何事,也无法真正参与其中,只是一个被动的旁观者。
感觉活得没有意思,因此去死的人可能不多,但处于这种状态的人一定不少。这种弥漫性的、慢性的无意义感,像时代的暗流,潜伏在许多看似正常的生活之下。它可能表现为对一切都提不起兴趣,对人际关系感到疲倦,对未来没有任何期待,只是在惯性的轨道上滑行。
一个高一男生,不愿去上学,父母逼急了就离家出走,最后辍学在家。他每天无所事事,除了玩手机啥也不干,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父母没收手机,断掉网络,无所谓,他就在床上一躺一天。对未来有什么打算?没打算。如果父母不在了怎么办?就去死呗。他的生活失去了所有内在的驱动力,外在的奖惩(如父母的压力、学业的成败)对他也不再起作用。他像是提前进入了精神上的冬眠,关闭了所有感觉通道,以一种最低能耗的方式维持生命体征。
张道龙老师将这种状态,称作“无欲状”。这是一种意志的瘫痪,欲望的枯竭。不是“想要而不得”的痛苦,而是“什么都不想要”的死寂。这种状态比抑郁更棘手,因为治疗通常需要依靠来访者内在的改变动机,而当动机本身消失时,干预便无从着力。
“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东西能让我开心,我觉得活着死了都行。”我自己的一个亲人也说过这样的话。这句话平静得可怕,它宣告了与世界的彻底脱钩。快乐、痛苦、成就、失败……这些构成生命张力的两极,对他而言都失去了差别。活着,仅仅是一种生物性的延续,与一颗植物无异。
就是在这种状态下,维罗妮卡决定去死。自杀对她而言,不是一种冲动的逃避,反而像是一种主动的、清醒的、对无意义生命的最终裁决。是她唯一能完全由自己掌控、并能产生确定结果的行为。
她吃了四盒安眠药,但没死成,被送到维雷特抢救。维雷特是一座令人生畏的精神病院,由一所废弃的军营改造而成。这里收容着被社会判定为“异常”的灵魂,是一个与现实世界规则迥异的“异托邦”。她活过来了,却被伊戈尔医生告知,因为滥用麻醉剂,心脏受到了无法挽回的伤害,她只能再活五天,最多一周。这个诊断,像一道突如其来的闸门,将她从无休止的灰色时间流中猛地截停。
伊戈尔医生让全院的人,都知道这一消息。这不仅仅是一个医学告知,更是一个社会情境的设定。突然间,维罗妮卡被赋予了“将死之人”这个全新的、极具冲击力的身份。这个身份像一束强光,照射进她空洞的生命,投下巨大的阴影,也照亮了此前未被察觉的角落。
死期被延长了一周,幸耶?悲耶?对于一心求死的她,这似乎是额外的折磨;但对于那个未曾真正活过的她,这被迫缩短且界限分明的一周,是否会成为唤醒生命意识的最后契机?当终点清晰可见,每一分秒的流逝是否才开始有了重量?
-02-
这是我第二次读这本书。第一次读的时候,我尚没有接触心理学,因此我是维罗尼卡。那时,我深深共情她的虚无与绝望,觉得她的选择虽极端却可以理解,甚至在她身上看到了现代人共有的精神困境的缩影。她的故事让我感到一阵悲凉与战栗。
这一次,我是伊戈尔医生,同时,我也是维罗尼卡。作为“伊戈尔医生”,我试图理解他干预策略背后的心理学逻辑:他如何利用“死亡预期”这一极端情境,来制造一种“存在性休克”,从而打破来访者僵化的心理防御,激发其最原始的生命力。作为“维罗尼卡”,我再次体验那种从麻木到苏醒的惊心动魄,但更多了一份对疗愈可能性的观察与思考。
当一个人不因为任何现实原因而一心寻死,这恐怕是精神科医生或心理咨询师遇到的最大挑战。因为干预无法从解决具体问题入手(因为没有“问题”),也无法依靠消除症状来达成目标(因为“空心”本身可能就是唯一症状)。这需要治疗师超越技术层面,深入到哲学与存在意义的领域,与来访者共同进行一场灵魂的探险。
你焦虑,我可以治,你抑郁,我可以治。一个人的“空心”或“无欲”,怎么治?焦虑和抑郁往往有明确的情境、认知或生理基础,有相对成熟的药物和心理治疗方案。但“空心”触及的是价值层面,是意义的危机。药物可以调节情绪神经递质,却无法赋予人生意义;传统的认知行为疗法可以调整不合理信念,却难以应对“没有任何信念”的空白。
徐凯文老师发现,对于“空心病”,药物无效,传统的心理治疗方法无效。这是一个令人警醒的发现。它提示我们,当心理问题根植于价值观和存在意义的缺失时,仅仅着眼于症状缓解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有更深层的、触及灵魂的对话与引导。
很多时候是,症状治没了,但他的人生还在。如果没有什么东西填满他的空虚,他依然是一具行尸走肉。治疗可能让他不再失眠、食欲恢复、甚至能进行社交,但他内心深处的空洞感、无意义感依然存在。他可能学会了“扮演”一个正常人,但内里依然荒芜。这种“治愈”是不彻底的,甚至是危险的,因为他可能更加娴熟地隐藏自己的痛苦,直到下一次崩溃。
徐凯文老师分享了他的一次探索:
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北大学生,学习优异、人际关系良好、没有任何现实的原因,但他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他内心不相信任何人,也不相信世界上有任何美好。这种“不相信”是“空心病”的坚固外壳。它不同于偏执,而是一种深刻的、悲观的虚无主义,认为一切美好、崇高、真挚背后都是虚幻、利益或偶然。
徐凯文老师在跟他交流的过程中,谈到了一件事情。在北大未名湖畔一个很偏僻的角落,有一座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先生的雕像。北大校园里有很多伟大人物的雕像,但惟有蔡元培先生的雕像前一年四季都有鲜花。也许是师生,也许是游客在蔡元培先生的雕像前敬奉上鲜花,有的还会写下他们的内心感受。
这个细节之所以重要,在于它的“非功利性”。献花没有任何现实的回报,它纯粹是一种情感的、价值的表达。它证明了在实用主义和功利计算之外,人类精神中还存在对理想、对先驱、对某种超越性价值的自发敬仰与怀念。
这是因为什么呢?他告诉学生说,虽然蔡元培先生已经过世很久了,也不是中国主流的政治人物,但是他对北京大学的贡献,他所传承下来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精神,永远铭刻在每个北大人以及来访问的游客心中。这个世界虽然有这样和那样的糟糕的部分,但真、善、美还是时刻存留在我们内心当中。这番话试图在来访者坚硬的虚无主义外壳上撬开一道缝隙,让他看到人类集体潜意识中对于“真、善、美”的永恒追求与守护。它不否认世界的糟糕,但指出糟糕并非全部。
当他跟那位学生讨论到这一点的时候,学生告诉他说:“我非常感动!”而且连说了三次。后来,那个学生再没有寻死。“感动”是疗愈的关键转折点。当一个人被虚无冰封的情感开始融化,重新感受到“感动”这种联结自我与更高价值的情感时,改变的种子就播下了。感动意味着他重新与某种美好、崇高的事物建立了心理联结,这种联结提供了归属感和意义感。
徐凯文老师的探索方向是,帮助空心病的来访者找回他们失去的心灵。那就是找到幸福感,找到亲密关系,找到成就感。他认为那些高尚的情感,比如善良、公正、诚信、尊重和责任感,能让一个人的内心更加充实,帮助一个人看到更美好的自己,让人体会到人生之美、人性之美。这条路径强调重新建立与积极价值观、与他人、与有意义活动的联结。它不是灌输教条,而是引导来访者去发现、体验和确认那些能真正触动他们内心、让他们感到“活着”的东西。
当我听到这个案例时,我也很感动。今年暑假女儿去北大游学,我给她讲了这个故事,她专门去瞻仰了蔡元培先生雕像。这个跨越两代人的讲述与行动,本身也成了一种意义的传递。它让我看到,对抗“空心”不仅是专业的治疗课题,也是每个家庭、每个教育者乃至整个社会需要思考的命题。我们如何在追求成功与效率的同时,呵护那些滋养心灵的、非功利的价值与情感?
-03-
对于一心寻死的维罗妮卡,伊戈尔医生用了什么样的办法呢?
他告诉她,她只能再活五天,最多一周时间。当她在维雷特游荡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知道她是将死之人。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社会实验”。伊戈尔医生人为地创造了一个极端的“濒死情境”,并将这个情境公开化、社会化。维罗妮卡被迫进入一个全新的角色脚本,周围人对她的态度、期待和行为模式也随之改变。这彻底打破了她原有的、令人窒息的生活剧本。
面对将死之人,每个人、每件事都变得很微妙。包括维罗妮卡自己。主动寻死是一回事,等待死亡又是另一回事。前者是一种对无意义生命的主动终结,带着一种决绝的控制感;后者则是在有限时间内被动地体验“活着”,死亡从抽象概念变成了具体倒计时,迫使她重新审视每一个当下的体验。
维罗妮卡会用人生中的最后五天做什么呢?她做了一些从来没做的事情。反正这里就是疯人院,疯狂一些很正常。维雷特这个“异常”空间, paradoxically 为她提供了“正常”世界所不允许的自由。在这里,社会规训暂时失效,她可以卸下“好女儿”、“好职员”的面具,探索那些被压抑的、被视为“疯狂”的自我部分。
当觉得自己受到嘲笑时,她狠狠地打了那个老男人一记耳光。这是攻击性的释放。在“文明”社会里,攻击性常常被压抑或转化为内耗。维罗妮卡这一耳光,是她对自己长期被动忍受、不敢表达愤怒的一种颠覆性反击。通过这个行动,她重新感受到了自己的力量和边界。
在这里,她是个疯子,她不需要取悦任何人。但是,她还是太正常,需要别人告诉她:不要成天想你会让别人不自在。如果其他人不喜欢,他们会提出来的。如果他们不敢提,那就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了。这句话点破了许多“空心”或抑郁者的一个心理模式——过度关注他人评价,并将想象中的评价内化为对自己的苛责,从而不断压抑真实自我以适应外界。在维雷特,这条规则被颠倒了:真实表达是第一位的,他人的反应是他们自己的课题。
他打了那个老男人,又与护工起了冲突。她恨自己,恨世界,恨此时能想起的一切。她对世界上自己最爱的人产生恨意,那就是母亲,那个把爱全给了她的人。她仇恨母亲给她的爱,因为她竟然不要一点回报。恨意的涌现,是情感复苏的强烈信号。长期麻木之下,连恨都感觉不到。她对母亲的恨尤其复杂,可能混杂了因无法回报而产生的愧疚、因无微不至的爱而感到的窒息、以及对这种“完美之爱”背后可能隐藏的控制的无名愤怒。感受到恨,意味着她开始区分自我与他人,开始建立心理边界。
她感受恨意汹涌。让情感流动,无论是恨是爱,都好过一潭死水。情感是生命的动力,即使是负面情感,也证明人还在感受、还在反应。
恨意退场,爱意萌生。她开始弹琴,弹给星星、花园、远山。艺术表达成为她情感的出口和升华。弹琴不再是为了表演或取悦,而是为了与自然、与宇宙进行纯粹的交流。这是一种超越功利的美学体验,连接了她与更大的存在。
这时,一个疯子出现了。他叫爱德华,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根本治不好。她弹给他听。爱德华作为另一个层面的“边缘人”,成为了她最真诚的听众。这种联结超越了理智与疯狂、健康与疾病的世俗界限,是两颗孤独灵魂在最本真层面的相遇。在他面前,她无需任何伪装。
她想在快乐与欢愉中死去。她想感受到更强烈的快感。她脱光自己的衣服,一丝不挂地站在爱德华面前,然后忘我地手淫。这是对生命本能和性欲的彻底解放与探索。在“正常”社会被严密规训的性与身体,在这里成为了探索生命愉悦、确认自我存在的直接途径。这行为惊世骇俗,但在她的情境下,却是一种向着生命原力回归的仪式。
她快乐地飞上了天。她体验到了极致的、纯粹的感官愉悦。这种体验本身,就是对“活着没意思”最有力的反驳。它证明了生命内部蕴藏着丰富的、强烈的感受可能性。
她完整地探索了自己的生命。从恨到爱,从攻击到创造,从孤独到联结,从压抑到释放。在短短几天内,她以浓缩的、 intensified 的方式,体验了生命光谱的多个极端。这种高强度、高密度的体验,像一次电击治疗,重启了她麻木的感官和情感系统。
……
当护士告诉她她的生命还有最多24小时时,她提出了两个请求,一是开一种药让自己一直清醒,好好地过剩下的每一分每一秒。二是离开维雷特,在外面死去。此时,她的心态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变:从“渴望结束无意义的生命”变成了“渴望充分体验最后的有意义的时光”。她想要清醒地、主动地去生活,哪怕只剩一天。她想回到“正常”世界,不是以从前那个麻木的过客身份,而是以一个即将逝去、因而无比珍惜的参与者的身份。
在生命的最后24小时,她想做什么呢?
她说:
“我要爬上卢布尔雅那的城堡,从前我总去那里,可是从来没有在近处好好看过它。我想和那位冬天卖栗子春天卖鲜花的大婶说说话。我们总是擦肩而过,可我从来不曾问候她一句。我想不穿外套,在雪天里走走,感受屋外的寒冷。从前我总是捂的暖暖和和的,唯恐得了感冒。” 这些愿望平凡而具体,关乎对日常细节的深度感知,对陌生人的温暖联结,以及对自然元素的直接体验。它们代表着一种“在世存在”的重新苏醒——用心去看,去感受,去交谈,去体验冷与热。
“我想让雨水打在我的脸上,我想向对我有兴趣的男人微笑,如果他们请我喝杯咖啡,我一定接受邀请。我要吻我的母亲,告诉她我爱她,在她怀里大哭一场。” 这里是对浪漫可能性的开放,对亲密情感的勇敢表达。从前可能因矜持、恐惧或麻木而错过的联结,现在都变得珍贵而值得追求。对母亲的吻与泪水,是情感堤坝的最终决口,是爱与愧疚、依赖与独立的复杂和解。
“也许,我会走入教堂,看着那些雕像,他们从不曾和我说过一句话,但是这次,也许他们会和我说点什么,如果一个有趣的男人邀请我去舞厅,我会接受,我会整夜跳舞,直到精疲力尽。然后我会与他共度良宵。” 这里包含着对超越性(宗教体验)的开放性,以及对世俗欢愉(舞蹈、性爱)的全身心投入。她愿意尝试一切能让她更深刻感受生命的方式。
“我想投入地爱男人,投入地爱这个世界,投入地度完这个生命,最后,投入地死亡。” “投入”是关键词。与开篇的“无所谓”和被动接受形成鲜明对比。她渴望的是一种全情投入、充满激情与参与感的存在方式。连死亡,她都希望是“投入地”,即清醒地、完整地体验生命终结的过程,而非浑浑噩噩地消逝。
这些文字深深打动了我。这才是生命本来的样子。生命本来的样子,不是按部就班地完成 checklist,而是在有限性中,带着觉察、勇气和热情去体验、去创造、去联结、去爱,也包括去恨、去痛苦。是让情感流动,让自我展现,哪怕会受伤、会犯错。
维罗妮卡没有死。她只有一周的生命,是伊戈尔医生的一个”谎言“,或者叫一个实验。他制造了她要死于心脏病的假象,为的是唤醒她的死亡意识。因为,“死亡意识激励我们活得更久”。这个实验的本质是“以死观生”。当人真切地意识到生命的有限和死亡的必然时,反而能激发出对生命最大的热情与创造力。死亡作为背景板,让生的色彩骤然鲜明。
伊戈尔医生的”死亡实验“告诉我们:自由地表达攻击性、恨意、性、爱,一个人就可以向死而生。疗愈的关键,在于解除对真实自我的压抑,允许被社会规范所禁止或污名化的情感与欲望(攻击性、性欲等)得到表达和整合。当一个人能够完整地接纳和表达自己的各个方面,而不是将其割裂或压抑,他就能获得一种更完整、更富有生命力的存在感。
但,可悲的是,只有在维雷特,一个人才能自由地表达。是什么,让维罗妮卡们,不敢在日常生活中,活出像在维雷特中的样子?这个问题直指社会文化的核心。我们的家庭、学校、职场和社会规则,是否在无形中压抑了真实的情感和个性的表达?是否过度强调一致、服从、功利和表象的和谐,而牺牲了内心的多样性与活力?是否将“正常”定义得过于狭窄,以至于许多健康的生命冲动都被贴上了“疯狂”、“不当”、“幼稚”或“无用”的标签?维雷特作为一个“异域”,映照出了“正常”世界的某种病态。真正的挑战或许在于,如何在我们日常的“正常”世界里,为每一个独特的灵魂,创造一点能够“自由呼吸”、真实存在的空间。
作者简介:代桂云
热门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