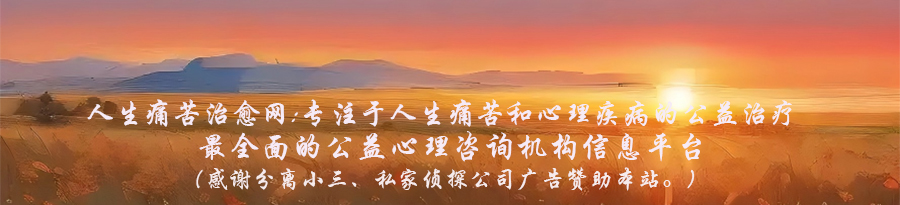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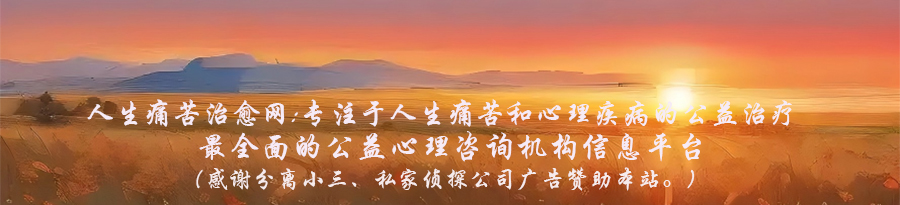
生命的最后一课必定是衰老和死亡。
然而,死亡教育一直都是我们成长过程中缺失的一块,我们总是怀着喜悦的心情来迎接新生命,却很习惯对生命将走向结束而闭口不谈。我们的文化似乎更擅长庆祝开端,而将结局包裹在沉默、忌讳与隐隐的恐惧之中。我们学习如何喂养婴儿,却不知如何陪伴临终的老人;我们热烈讨论如何活得精彩,却对如何有尊严地离去三缄其口。这种集体性的回避,使得当死亡不可避免地降临时,无论是逝者还是生者,都常常陷入 unprepared(毫无准备)的慌乱与痛苦之中。
“这些病人都早已知道自己病入膏肓,然而他们,连同他们的家人,都没有为最后的阶段做好准备。”
这句话让我破防了。它尖锐地指出了我们面对死亡时普遍存在的一种悖论性困境:明知结局就在前方,却依然像把头埋在沙子里的鸵鸟,拒绝或不敢去为那必然到来的时刻做任何实质性的规划和心理建设。我们仿佛被一种强大的惯性推着走,直到撞上那堵名为“死亡”的墙,才惊觉一切都已太迟,留下的是无尽的悔恨、困惑和未竟的话语。
距离爷爷去世已经有半个多月了,对于我而言,最大的缺憾,就是没能够和爷爷好好告别。这份缺憾并非源于未曾陪伴,而是源于我们之间那层薄薄的、由“善意谎言”织成的纱幕。在纱幕的两边,我们各自扮演着“保护者”和“被保护者”的角色,却因此错失了最真实、最深刻的连接机会。那声最终的“再见”,成了一场心照不宣的、无声的哑剧。
爷爷是癌症晚期,全家人都没告诉他真相,咨询多位医生后,我们了解到,治疗反而徒增病人的痛苦,甚至还可能更早离开。这个决定,是在极度的爱与无措中做出的。我们被推到了道德与情感的十字路口,一边是对“知情权”的模糊认知,另一边是对亲人免受折磨的本能保护欲。现代医学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更是加剧了这种选择的艰难。我们被各种可能性、数据和专家的意见所包围,却唯独听不到那个最应该被倾听的声音——爷爷自己,想要如何度过他最后的时光。
我们一方面,担心犯下延长病人痛苦的错误,另一方面,害怕因为自己的预判失误,没有足够长地保持病人的生命。经过内心的一番挣扎,我们选择了放弃治疗。这个“放弃”,在情感上是沉重的,它伴随着“是否足够努力”的自我拷问,以及来自社会文化中对“尽力救治”这一伦理标准的潜在压力。我们仿佛在“延长生命”与“保障生命质量”之间,进行着一场没有赢家的拔河。
我们对爷爷说了善意的谎言,让他安心休养。很欣慰的是爷爷的精神状态一直不错,也没有受过癌痛,去世前两天,还独自坐公交去镇上了。那时的我们,或许将这视为一种“成功”——爷爷在平静中走完了最后一段路。我们为他的“不知情”而感到一丝庆幸,仿佛帮他躲过了一场名为“绝望”的风暴。但这份庆幸,如今看来,却混合着苦涩的疑问:我们真的保护了他吗?还是,我们其实也剥夺了他面对自己生命结局、进行内心整理和告别的权利?
然而,意外总是来得猝不及防,在家摔了一跤后不到两天,爷爷就走了。那看似平静的日常,被一个偶然的跌倒彻底击碎。死亡不是按部就班地沿着医学预判的曲线下滑,它常常是这样,带着一种戏剧性的、粗暴的突然性,闯入我们的生活。我们精心维持的“平静休养”的表象,瞬间瓦解,将我们抛入措手不及的永别之中。
爷爷的离开让我感到难以接受、无比伤痛的同时,更是非常遗憾和自责,甚至质疑自己:当初瞒着爷爷的病情做法是否正确?是否剥夺了爷爷自己从容地处理人生终点之事的权利?我们真的了解爷爷的需要吗?这些追问在寂静的夜里反复回响。我回想起爷爷最后的日子里,他是否曾有过欲言又止的时刻?他望向窗外的眼神里,是否藏着对生命终点的某种直觉或疑问?而我们,出于“保护”,是否用我们的爱,无意中筑起了一堵墙,让他独自面对那最终的黑暗,却无法与我们分享一丝恐惧或期待?我们自以为是的“为他好”,是否恰恰成了横亘在生死之间的最大障碍?
人们大多因为忌讳总是避开讨论和思考疾病和死亡,以致在必须面对时而惊慌失措。这种忌讳像一种社会性的传染病,从家庭蔓延到社群,甚至渗透进医疗系统。我们回避谈论,仿佛不谈,它就不会发生;我们不提前思考,仿佛思考就是一种不祥的预兆。结果便是,当死亡来敲门时,我们手忙脚乱,只能依据最本能的恐惧和外界最通用的模板(通常是“不惜一切代价抢救”)来应对,往往忽略了逝者本人最核心的意愿和需求。
而往往是在经历重要他人的离开时,才会去思考:到底什么是生与死?如何面对衰老和死亡?死亡像一位最严厉的老师,它不提前备课,直接进行一场残酷的现场教学。只有当我们被失去的痛楚击中,才会被迫睁开眼,去看那个我们一直逃避的课题。然而,在巨大的悲伤和混乱中进行的思考,往往是片面的、充满情绪的。我们多么希望在失去之前,就能拥有一些关于告别的智慧和勇气。
美国著名外科医生,哈佛医学院教授,阿图·葛文德在他的《最好的告别》一书中,通过自己在行医生涯中的所见所闻,以及对死亡的思考,提出了该怎样正确面对生死。这本书像一束光,照亮了那个我们习惯性回避的黑暗角落。它没有提供简单的答案,而是带领我们进行一场关于医疗局限、人性需求、自主尊严的深刻反思。它告诉我们,现代医学在延长寿命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却在如何面对生命的终结上,常常显得笨拙甚至有害。我们需要一场观念的革命,从“不惜一切代价对抗死亡”,转向“如何让生命的最后阶段依然保有意义和尊严”。
01 认识衰老
你有没有想过,自己究竟是如何衰老的?我们通常将衰老视为一个缓慢、均匀的衰退过程,就像一件物品随着时间流逝慢慢磨损。但事实可能比这更复杂,也更脆弱。
研究表明,人之所以会变老,是因为随机损耗的结果。这听起来有些令人沮丧,它意味着衰老并非一个精心设计的程序,而更像是一场在分子和细胞层面不断累积的“意外”和“故障”。我们的身体像一台极其精密的机器,在数十年无休止的运转后,零件会以难以预测的方式逐渐失灵。
一个衰老的过程就是一个身体崩溃的过程,如果要很形象地画出一个曲线来表示的话,一个人的健康状态可以一直处于平稳的直线,但到了七八十岁,看起来还是不错的,然后就会突然有一天,啪的一下,急速下降。这条曲线被医学研究者称为“断崖式下跌”。它揭示了老年人健康的脆弱性:他们可能长期维持在一个虽然不高但尚可的水平上,但储备能力(生理韧性)已经非常稀薄。一次轻微的感染、一次不起眼的跌倒、甚至是一次情绪上的重大打击,都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导致身体机能的全面崩溃。
衰老是一个突发事件,一个老年人可能会一直看着很健康、很好,即使到了70多岁还好好活着,但一旦遇到了一点小问题或者意外,他就会快速地下滑。因此,看待老人的健康,不能只看他们“现在”能做什么,更要看他们的“储备”还剩多少,以及他们抵御微小冲击的能力有多强。这提醒我们,对老人的关爱,预防远胜于治疗,创造一个安全、支持性的环境至关重要。
书中还提到了老人疾病常识:比如,脚才是老年人真正的危险,老人面临的真正威胁是跌倒,因为跌倒导致髋关节骨折。世界上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老人都是因为摔了一跤离世的。这个数据令人震惊,也颠覆了许多人的常识。它告诉我们,维持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往往不是攻克某种绝症,而是保障最基本的安全——一双合脚的防滑鞋,家里无障碍的通道,稳固的扶手,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可能就是决定一个老人是继续独立生活,还是从此卧床不起、走向生命终点的关键。预防跌倒,是老年医学和养老中至关重要的一课。
02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怎样才是真正的活着?
健康专业人员有一个系统的标准来评估一个人的身体功能。如果在没有他人帮助下不能完成“八大日常生活功能”:如厕、进食、穿衣、洗浴、整容、下床、离开座椅、行走,那么你就缺少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这些功能是维持一个人独立生存尊严的基石。每丧失一项,就意味着对他人的依赖增加一分,自我掌控感减少一分。
如果不能完成“八大日常生活独立活动”:自行购物、做饭、清理房间、洗衣服、服药、打电话、独立旅行、处理财务,那么你就缺少安全独自生活的能力。这些活动代表着一个人与社会的连接和自主管理生活的能力。它们的丧失,往往意味着一个人从社会生活的积极参与者,逐渐退回到一个需要被全面照料的“被抚养者”角色。
我们总有一天,会无法胜任这些在现在看来十分简单的任务。认识到这一点是残酷的,但也是必要的。它迫使我们提前思考:当那一天到来,什么对我们来说才是最重要的?是仅仅“活着”,还是以某种我们认可的方式“生活”?
变老的过程,就是一系列连续不断的丧失。我们会亲自经历失能、失明、失智,失去最好的朋友和固有的生活方式,甚至生活品质逐渐下滑,最后滑向深渊。这是一场漫长的、不可逆的告别。它不仅是对身体功能的告别,也是对熟悉的自我形象、社会角色和生活世界的告别。承认并哀悼这些丧失,是晚年心理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我们年老、体弱、不能照顾自己的时候,是什么使生活值得过下去?这是存在主义的核心追问,也是每个走向生命终点的人无法回避的问题。如果生命只剩下病痛、依赖和无尽的医疗干预,活着本身是否还是一种福祉?
答案是:简单的愉悦和自主有意义的生活。这个答案朴素而深刻。它剥离了繁华与成就,回归到生命最本真的需求。当宏大的目标变得遥不可及时,那些微小的、日常的快乐和自主选择的权力,就成了支撑生命意义的关键支柱。
随着年龄增长,我们都学会从简单的愉悦中寻求慰藉——友情、日常的例行公事、好食物的味道,以及阳光照在脸上的那种温暖。这些体验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它们连接着我们与世界的真实触感,证明我们依然在“感受”和“存在”。一场与老友的午后闲谈,一个固定的散步路线,一口喜欢的点心,一缕照进房间的阳光,都能成为一天中的亮点,成为继续活下去的理由。
怎样才是自主有意义的生活?我们所要求的就是可以做我们自己人生故事的作者,按照忠诚于自己个性的方式,塑造自己生活的自由。自主,并不意味着完全独立,不依赖他人。相反,在年老体弱时,自主往往意味着:即使在需要帮助的情况下,我依然能对我的生活有发言权。我想吃什么?我想几点起床?我今天想见谁?我想如何度过我的时间?这些看似微小的选择权,是尊严的核心。当一个人连这些选择都被以“为你好”的名义剥夺时,他/她就从生活的主体,沦为了被处理的客体。
最好的告别,也许是让自己哪怕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可以拥有对生命的掌控能力,有尊严地跟这个世界告别。这意味着,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治疗的程度和方式,决定最后时光在哪里度过、和谁一起度过,甚至决定以何种方式离开。这是一种终极的自主,也是对生命最后的、最深刻的尊重。
03 面对患病的亲人,到底该怎样做才是正确的选择?
作者指出:当一个人大限将至时,家人应该做的二种正确选择:那就是尽力治疗和善终护理。这并非一个非此即彼的单选题,而是一个需要根据病情阶段、治疗可能性和病人意愿进行动态权衡的 continuum(连续谱)。关键在于,选择的出发点应该是病人的整体福祉(包括身体舒适、心理安宁和意愿实现),而非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延长。
对于重病患者来说,除了单纯地延长生命,还要考虑如何减轻病人的痛苦,并尽量满足病人的内心需求,这才是对患者最好的尊重。现代医学常常专注于“治病”,而忽视了“治人”。当疾病无法治愈时,医疗的目标就应该从“治愈”(cure)转向“照护”(care),即缓解症状、控制疼痛、提供心理和精神支持,帮助病人以尽可能舒适和平静的方式走完最后一程。
当然,对于通过治疗可以挽回生命的,就应该积极配合医生尽力治疗;这里强调的是治疗的有效性和目的性。如果一种干预措施有较大可能让病人恢复有质量的生活,那么积极治疗无疑是正确的选择。关键在于,要对“挽回生命”有清醒的认识:挽回的是怎样的生命状态?病人需要为此承受多大的痛苦和代价?
而对于危重病人,特别是需要上各种器械才能延长生命的,最好就不要治疗了。因为,过度治疗不仅徒增病人痛苦,可能连和亲人最后说再见的机会都没有了。ICU(重症监护室)里的情景常常如此:病人全身插满管子,在镇静剂作用下昏迷,与家人隔离。生命体征或许被机器维持着,但作为“人”的体验、连接和告别,却完全丧失了。这种“活着”,更像是一种生物学上的“存在”,而非有意义的“生活”。它剥夺了病人与家人进行最后情感交流的机会,也常常让家人在病人去世后,留下“没能好好告别”的终生遗憾。
而如果选择放弃治疗,有家人陪在病人身边,不仅能给他们最大的安慰,还可以让病人感受到亲情的温暖。让患者平静、安祥地离开这个世界,不仅是对患者,也是对亲人的最大慰藉。善终护理(Hospice care)或安宁疗护,正是为此而生。它不加速死亡,也不刻意延长死亡过程,而是提供专业的疼痛和症状管理,以及心理、社会和精神层面的全面支持,让病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能够在家或像家一样的环境里,被爱包围,有尊严地离去。这种“好好的死”(good death),对于生者而言,也是一种重要的疗愈过程,让他们感到自己已经尽力给予了亲人最好的陪伴和关爱。
阿图的父亲也是一名成功的医生,对于疾病有着客观的认识。当父亲进入了癌症晚期,阿图医生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那就是和身为病人的父亲进行了一次谈话,谈话的主题是一个临终的人真正需要的是什么。这次谈话是革命性的。它跳出了“医生-病人”或“儿子-父亲”的传统角色,而是两个对生命和死亡有深刻理解的成年人,就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进行的平等交流。它开启了关于真实意愿、恐惧和期望的对话。
在阿图医生的这次谈话中,阿图医生和父亲达成了共识,那就是善终并不是关于如何好好接受死亡的话题,而是关于如何好好走完生命的全程,他们心里很清楚,死在医院里的患者,往往都会在生命的最后一个阶段承受着大量的治疗和痛苦。因此,重点从“如何死”转移到了“如何活到最后”。他们关注的是,在剩余的时间里,如何最大化生活的质量,如何保持那些对父亲来说最重要的东西——也许是头脑清醒,也许是能够与家人交流,也许仅仅是避免痛苦。
所以在积极治疗之外,医生还可以给其他选择,也就是仅仅给予一些减轻痛苦的治疗,让病人有尊严地死亡。这被称为“舒缓治疗”或“安宁缓和医疗”。它承认医学的局限,将目标从“治愈疾病”调整为“提升生命末期的舒适与尊严”。这需要医生有勇气与病人及家属进行困难的对话,也需要社会观念从“放弃治疗等于放弃亲人”的误区中走出来。
阿图医生的父亲在经过思考之后,最终也选择了这种方式,在那天下午,他仔细地看了家里孩子的照片,看了自己的每一个亲人,然后便陷入昏迷,几个小时候之后他停止了呼吸,他的儿子和妻子都在他的身边。这个场景是对“善终”最生动的诠释:他在熟悉的环境中,被所爱之人环绕,意识清醒时完成了内心的告别,然后平静地离去。没有惊慌的抢救,没有冰冷的仪器,只有温暖的陪伴和自然的生命进程。这是一种有准备的、被温柔接纳的死亡。
04 最终的告别
“告别”这个词和“离别”一样往往充满感伤,而人生中生离死别的“永别”,更是让人无法接受和面对。但回避只会让告别变得更加仓促和充满遗憾。学习告别,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补上的一课,它关乎如何结束,也反过来影响我们如何理解生命。
我们该如何好好与亲人做好“最终的告别”呢?心理咨询师指出以下几点:
(1)帮助病人完成未了的心愿
一个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病人,他的关注点已经更多变成了如何避免痛苦,加强和亲人及朋友的联系,担心自己死后爱的人如何生活,以及能够在生命终结之时,完成未能完成的愿望,哪怕这个愿望非常简单。这些心愿可能非常具体:想见某个多年未见的老友,想去某个地方再看一眼,想吃到某种食物,想对某人说一声“对不起”或“谢谢你”,甚至只是想确认家人会好好生活。协助完成这些心愿,是对病人生命故事最珍贵的补全,也能给生者带来莫大的安慰。
也许,若时光可以倒流,我会勇敢一些,好好地和爷爷交流,表达我对爷爷的爱与不舍,了解爷爷有哪些未完成的心愿,有哪些最想见的人,最想做的事,并帮助爷爷去实现。我会坐下来,握着他的手,不再回避他眼神中可能存在的疑问,而是轻声问他:“爷爷,您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做的事,或者想见的人?我们一起来想办法。” 哪怕他的心愿只是再听一次家乡的戏曲,或者去老屋门前坐一坐。
我想,爷爷一定想和这个世界做好最后的告别,我会引导爷爷用体面、优雅、有尊严的方式,和爱的人说再见。或许是通过录一段话,写一封信,或者仅仅是在一次家庭聚会中,进行一次正式的、充满爱意的道别。让告别成为一种有意识的、充满敬意的仪式,而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
(2)多陪伴
在病人清醒时多花时间去陪伴他(她),并多与病人互动,比如一起看家庭相册、视频,和病人讲以前的家庭趣事。陪伴的质量重于数量。放下手机,全然地在那里。不需要总是说话,安静的并肩而坐,握着手,也是一种深沉的连接。回忆往事,尤其是那些快乐的、温暖的片段,能帮助病人和家人都从当下的病痛和悲伤中暂时抽离,重新感受到生命中的爱与联结。这些共同的记忆,将成为逝者留给生者最宝贵的遗产。
(3)多表达
家人可以经常与病人保持对话,并经常解释自己正在做的事。家人也表达自己的感受,说出内心话,对即将离世的病人说“谢谢”、“对不起”、“我爱你”等。死亡临近时,很多平日里难以启齿的情感会变得异常清晰和重要。坦诚的表达能化解心结,让关系变得圆满。
“感谢”即将离世的家人曾经支撑过、参与过你的生命;说声“对不起”,对于过去的恩怨好好地和解;说句“我爱你”,圆满你们之间此生的缘分。这些话语具有强大的治愈力量,不仅对于聆听者是慰藉,对于诉说者也是一种释放和了结。它们能让死亡不再是关系中所有未竟事宜的终结,而成为一个带有完成感的句点。
(4)即使病人已昏迷了,仍可以感知到你的好好告别
听力通常是最后消失的知觉,病人即将离世时,其实会很挂念、不舍家人,但是因为只剩下最后一口气,无法表达情感,所以这时若家人能温柔坚定地好好和病人告别,不但可以让病人放心离世,家人在病人面前允诺“全家都会好好照顾自己”,不会让其担心,这份要好好活下去的责任感也会带给全家人力量。即使在昏迷中,亲人持续的、充满爱意的低语,讲述美好的回忆,表达感谢和爱,做出“我们会好好的”承诺,都可能被病人以某种方式感知到,带给他最后的安宁。这种告别,是对生命最深的尊重,也是对生者未来生活的郑重承诺。
对于至亲的人,离去,我们这一生终究会经历。认识生与死,尊重生命,好好告别,减少遗憾。死亡教育的目的,不是让我们变得麻木或无畏,而是让我们在必然的失去面前,能够多一些清醒,少一些慌乱;多一些温柔,少一些遗憾;多一些对生命本身的敬畏,少一些对医疗技术的盲目迷信。学会告别,是我们能为自己和所爱之人,上的最后一堂,也是最重要的一堂生命课。它教会我们,如何带着爱放手,如何带着记忆继续生活,如何让生命的终点,也能闪耀着人性的温暖与尊严。
文:李建学
热门文章